大约是我六七岁的时候,我们全校的小朋友都在泥泞的村子主路上,跳着舞、摇着花环、喊着口号,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地送一批解放军叔叔上前线。他们胸前戴着大红花,雄赳赳地列队前行,远远走出了村口用松枝搭起的高高凯旋门,我们的口号声还此起彼伏,一阵一阵成了每个班级的拉练。
后来才听老人说他们是去前线的支前民兵,那时认为穿上绿军装就是无比崇敬的解放军了,虽然没有红五星和红领章,没有我一个远房表叔穿绿军装的照片英武帅气。他在照片里一身绿军装红五星腰间别着手枪,一手掐腰,目光坚毅,一手佩戴着上海手表在指着军用地图。那张照片,简直占据了我小时候的憧憬和梦想,每天都要盯着相框看,每次都想象着照片之外是如何的炮声隆隆、枪声阵阵、震天动地。
那几年最盼望着这个表叔回来探亲,他一回来整个院坝里都围拢了乡亲父老,听他讲故事,传着看他的立功证书和奖章。我们小孩子最幸福的事,就是分到一小块压缩饼干,窝在墙角里舔着那种甜甜咸咸的味道,无限的甜蜜洋溢在小小院坝中。
再后来表叔光荣地从部队退伍回来了,他人长得高大英俊脑子又灵泛,在镇子里第一家开起了照相馆。过年过节我们都相约着去照相,穿上最想穿的衣服,坐在硬纸板做的雅马哈小摩托上,不断地更换着天安门、长城、大海、蓝天的背景,咔嚓咔嚓地留下了一张张开心的笑脸。尽管是手绘的背景、黑白的底色,但在暗房里冲洗后,根本看不出任何笑靥背后的皱褶。紧接着表叔又捣鼓起钟表修理,把那支黑黑的炮筒眼镜塞在双眼皮中,他可以在各种齿轮螺丝中坐一天到晚。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一排排挂在玻璃罩罩下面的电子手表,各式各样,花花绿绿。去他店里多少次,就看了多少眼。不敢要那些铁表带的广州货,心想哪怕是能有一块塑料表带的,也总比我画在手上的抖草。
表叔时不时地找我爸款嘴唠家常,他一进屋,我就猫出去悄悄地跨上他的28永久单车,双手扶龙头,屁股半坐在三角架上,双脚只能半圈半圈地踩。腿太短,稍微一不小心,半个屁股一条裤子上就沾满了泥巴或链条上的油污,甚至连人带车摔倒,被刮破皮撕烂裤子也是常有的事。从村头到村尾,掐算着时间差不多了,再偷偷地把他的座驾还回去。很多时候,是妈妈在大声叫唤,也有些时候是表叔和老爸在屋檐下抽着老烟筒,笑眯眯地等着我回去。
有一次不小心又撒远了,等我大汗淋漓急急忙忙地赶回去,表叔有事已经先回去了,这时候免不了一顿批斗。不过还好,还没等我委屈的眼泪掉在地上,妈妈笑呵呵地拿出了一样小礼物。呀!是表叔送我的一只电子表。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一块表,人生第一块手表!至少,我可以自己看着时间去上学;至少,我可以晚上睡觉时按一下,它的表盘就发出淡淡的优雅的绿光;至少,我在这么多的小伙伴中是第一个戴手表的人!
时间在滴滴哒哒中行走,季节在冷暖变化中交替。正月的大地千枝万树竟相发芽,田间地头的迎春花、羊耳朵花、苦刺花、棠梨花在风中摇曳,路头村尾的桃花姹紫嫣红、梅花红白相间,仿佛是一夜之间就全部绽放开来。二大爷家院子里的山茶树虬劲若云,年前就盛开的花朵端庄依旧、粉妆玉砌。田野里绿浪翻滚,一片片绿油油的青蚕豆、一条条金灿灿的油菜花、一个个亮晶晶的泛舟湖,春意浓浓的高原坝子万物复苏,生机盎然,遇见的每个人都在春风拂面中互致一年的问候。刚过的元宵节里互相“偷青”,象征性地在别人家地里摘几个青蚕豆、拔一颗青菜,也希望别人多到自己的菜地里踩青,才预示着一年的好运连连。春天的气息弥漫在每个人的心田,我们每天在菜花地里逐蝶撵蜂,玩累了就大把大把地吃着鲜嫩甜脆的蚕豆,捧一口甘甜的池塘水解渴,然后在豆田花海里美美地睡上一觉。冬春的池塘里水位下降,在露出的台地上,大人们辛勤地理出一垄垄整齐的水稻育秧地,那里的小苗正齐刷刷地排队出操。这个季节,我们要按照父母的安排,每天扛着一根竹篙穿着一个塑料瓢去给秧苗墒沟浇水,回来的时候还要在田埂上割一篮子青草喂兔子。
我每天都看着时间去浇水,生怕那些娇嫩的小苗渴着饿着,担心照顾不好会耽误了插秧时间。虽然我还没有竹篙的一半高,尽管我使出吃奶的力气还舀不满一瓢水,但还是要看着表在天黑前把墒沟里浇满水、背篮里割满草。波光粼粼的白水湖是我们家乡的宝,方圆十几个村子依湖而生、傍湖而建,炊烟袅袅、杨柳婀娜、鱼米飘香,半池出水芙蓉,一湖莲菱珍馐。整个的夏天,我和小伙伴们都泡在白水湖中,每次回家都要被妈妈在背上刮下一层层指印,她可以从指甲尖里的水气和印迹推断出那天游了几次澡。记得有一次农忙时妈妈叫我回家拿一个背篓,我直接套在头上装盔甲,结果一不小心掉在转角的池塘里,好在白水湖里练就的基本功成就了我,慌乱中,乱扑乱抓地游到了岸边,总算是捡回了一条狗命。
这些小沟小坝塘都不在话下,我们“扛过枪”、游过泳、翻过船、“打过仗”。记得有一天去浇水非常急躁,只想急着早点回去看电视,那段时间刚播完《霍元甲》又正在放《西游记》,小伙伴们都要来看,回去晚了,耽误了上房转天线,电视机一出雪花点那就把脸丢大了。反正是匆匆地浇水,随意地割了几把草,就小跑着赶回家。
第二天起床,才发现手表的时间不对了,没了灯光,没了跳动,是电池干了吗?还是按钮坏了?——天!我心爱的手表竟然只剩表壳和表带还在手上,电子表的表芯居然不见了!哦,是掉在哪里了呢?这手表,质量也太不靠谱了。急得我翻箱倒柜地到处找、到处回想,我好不容易的一块电子表呀,它到底去哪里了呢?害得我顺着昨天浇水割草的线路一点点搜索侦察、一点点扫荡回忆。这么个小孩,老天你为什么要叫他的表掉了呢?
秧苗长出了新芽,个头越窜越高,炎热的五月一到,它们就要被移栽到大田里继续安家。三四月间收完蚕豆,我们就跟着大队上的履带拖拉机去犁田翻地,我用纸画了一张表盘,紧紧地粘在我的手表表盘内,不时抬头看表,一手扶门一手指挥,同时想象着坐坦克指挥打仗的场景。
落实政策后,退伍回乡一年多的表叔去了有名的供销社,过几年他的坐骑换成了拉风摩托,戴着墨镜穿着喇叭裤行走在村社乡间,我的羡慕视野随之转移到他管的大仓库里,那里有高耸的物资、成垛的糖果和堆成小山的连环画,曾经我为了一辆小单车睡在百货公司的地板上滚来滚去,现在好歹可以饱饱眼福,有时候一整天就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如饥似渴地看那些连环画。大约是我上高中的那几年,随着企业改制表叔离开了供销社,干了一辈子,离开后他也想再创业,开过小厂、做过买卖、盘过餐厅、跑过保险,无奈总是诸事不顺。我工作后,听说表叔还是好喝酒,改不了酒多就话多事多的老毛病,还经常住院。去医院看他,他日渐消瘦,一见到我就诉说过去的辛酸,话少语轻,但俊朗的五官中仍有那么一些坚毅和硬挺。
和我祈盼的相反,他终是没有熬过那个冬天,在没满花甲的年岁惜别了他的战场。时间像是和我的表盘一样,掉在了白浪滔滔的白水湖中,看似停滞,但兜兜转转,它终究还是在另一个世界永生着。(燕刚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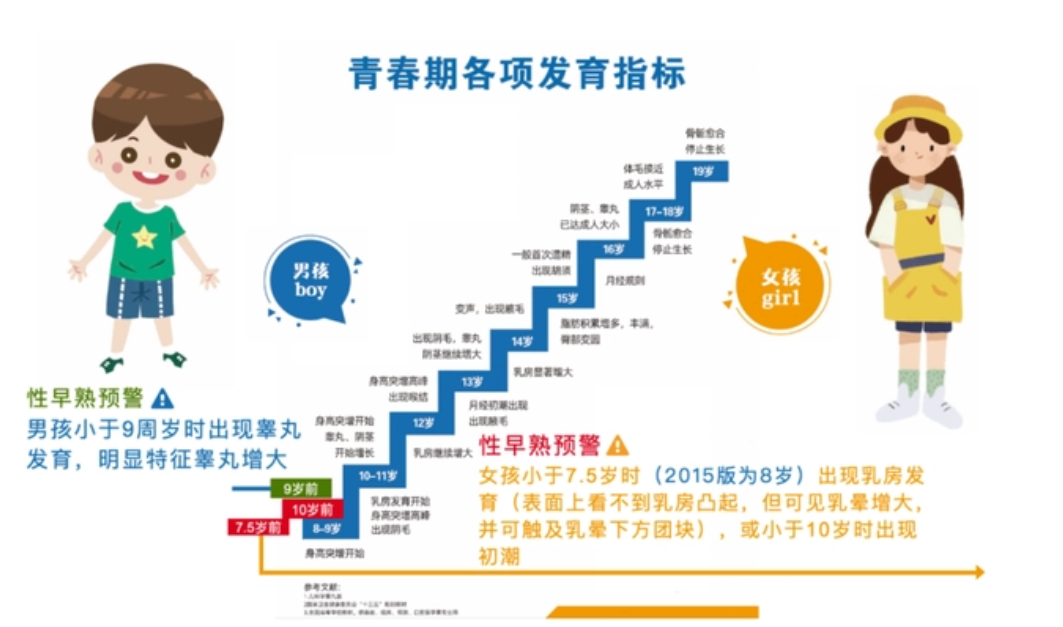
050b0da7-1806-43b5-a7a3-c7961f54d58d.jpg)